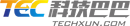做理论物理都追求简单?没那么简单!
2018-12-17 11:24:44 新浪科技综合 观点
我今年夏天参加过一场与高三学生的座谈,当时我问他们最简单、最著名的方程式是哪一个。很多同学说是1+1等于2,但我总觉得1+1等于2有点过于简单了,也没那么著名。再说1+1等于2,也不能算是方程式,而且物理学的方程式应该含有物理量。所以,往下看——
 演讲人 | 邢志忠
演讲人 | 邢志忠
最著名的物理学公式,毫无疑问是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E=mc2。为什么质能关系这个方程非常简单?因为它拥有意想不到的关联。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它把能量和质量关联起来。关联性是追求简单性的一个重要原则。
了不起的关联
爱因斯坦他老人家说了很多这方面的话。1932年的时候,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说,我们在寻求一个能把观察到的事实联系在一起的思想体系,它将具有最大可能的简单性。我们所谓的简单性,并不是指学生们在掌握这种体系时产生的困难最小,而是指该体系所包含的彼此独立的假设或公理最少。
1933年6月,他在牛津大学访问时强调,一切理论的崇高目标就在于使这些不能简化的元素尽可能简单,并且在数目上尽可能地少。
所以爱因斯坦他人家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能把时间和空间联系起来,能把质量和能量联系起来,能把万有引力和时空几何联系起来。将这些看起来毫无关系的东西联系起来,就使得理论非常简单,而且非常深刻。
因为简单,从而深刻,而不是反过来。或者说反过来也一样,因为要追求深刻,所以才追求简单。简单在很多时候是真理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也是它的力量所在。
举几个例子来体会一下。
狭义相对论的质能方程
比如说原子弹爆炸,是核裂变。原子核分裂前后有质量差,质量转化成了能量。
再比如核聚变。太阳为什么能发光发热?因为它的内部发生了核聚变。在这种巨变的过程中,能量产生出来,也是因为有质量差的原因。
 (图源:NASA/SDO)
(图源:NASA/SDO)
再举一个能量变质量的例子。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多信使天文学的时代,不仅仅是电磁波,中微子、宇宙线、引力波都成为我们探寻宇宙最深处的有效探针。双中子星合并或者其他剧烈的天体过程,产生了大量高能的光子。它们在宇宙空间中传播时,会和宇宙的微波背景辐射,也就是极低能光子,发生相互作用。两个光子相互作用会变成正反电子对。光子是辐射、是能量,而正负电子对是实体、是物质。这就是能量变质量的一个简单例子。
我们有非常多的例子来证明爱因斯坦的理论是对的。高能所地下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就是非常好的例子,其中电子或者正电子的速度是0.99999c(c为光速)。如果狭义相对论是错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控制如此高速的电子和反电子束流。
广义相对论的爱因斯坦方程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不再把引力理解成为一种力,而是时空在有质量的物体存在的时候,发生了一种几何形变。这就像一个平坦的蹦蹦床,放入了一个重的物体,它就会凹下去。时空的曲率和质能的分布,两者是等价。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思想。
首先提出现代黑洞理论、给黑洞起名的美国物理学家约翰•惠勒(John Wheeler)说过:Spacetime tells matter how to move, matter tells spacetime how to curve(时空告诉物质如何运动,物质告诉时空如何弯曲)。他的这番表述非常对称,非常好。
朗道(Landau)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方程可能是最漂亮的理论。朗道是非常挑剔的人,他都觉得是最漂亮的东西,那一定是最漂亮的。
所以苹果会从树上落下来,不一定要说苹果和地球之间存在万有引力。利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大质量的物体造成了时空弯曲,而所有的物体都有沿着测地线运动的趋势。因为当平面凹下去了之后,上面的小球当然要往凹的地方滚,所以苹果找的那条向下落的路,就是它认为最经济的路线(测地线)。
这是一种新的认识。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语言来描述同样的现象,这也是科学家应该具备的一个最基本的素质。
既然如此,时空都弯曲了,光就会走弯路。在上世纪初,英国科学家爱丁顿(Eddington)通过观察日全食证明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预言是正确的。确实,大质量物体存在的时空会发生弯曲,光沿着测地线走,就会走弯路。
 光线走弯路(图源:physics.stackexchange.com)
光线走弯路(图源:physics.stackexchange.com)
这让我觉得特别受启发。光也会走弯路,何况人呢?我们经常犯点错误,然后经常被老师或者家长,或者被其他人指责批评一番,这很正常。连光这么了不起的粒子,都会走弯路,我们人犯点错误,走点弯路,受点挫折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以我这么多年的人生经历所得到的最大的体会之一就是人怎样才能变得宽容:你把别人能犯的错误都犯了,你就会变得宽容,你就不太想指责别人了。因为同样的错误我自己也犯过,没必要再说别人了。
这也是为什么当年爱因斯坦他老人家在建立广义相对论的时候,不能再用欧几里得几何,一定要用黎曼几何。因为时空已经弯曲了。我们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有了新的物理思想,还要借助非常先进的数学描述。我们希望用最简单的数学方式来描述自然界背后最深刻的物理本质和物理规律,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统一
爱因斯坦他老人家追求简单,所有后来人做理论物理都追求简单,甚至还追求简约、节约,追求统一。统一了就会简单。我们已经实现了电和磁的统一,光和电磁波的统一,电磁力和弱核力的统一,时间和空间的统一,质量和能量的统一,但还有很多东西暂时还没有被统一起来。
大统一理论希望把电磁力和强弱核力都统一在一起。弦论追求的是a theory of everything(万物理论),把引力也统一起来,构建量子引力,当然还没有成功的理论来实现这一梦想。统一了就会简单;否则的话,不同的力要用不同的耦合参数来描述,而统一在一起的话,用一个耦合参数描述就可以了。
我们追求简单,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追求深刻、追求统一,追求一个完整的、大的物理图像。
美感
同时,我们需要借助比较好的数学语言,追求数学意义上的美感。复杂的表达通常都缺乏美感,简单的、对称的表达通常都具有美感。
我们从中学就学过e指数。著名的欧拉公式就特别的漂亮。费曼他老人家曾经说,这是the most remarkable formula in mathmatics(数学中最了不起的公式)。为什么?因为这个公式把自然界两个非常重要的参数——自然对数的底e和虚数单位i——联系了起来。
 (图源:science4all.org)
(图源:science4all.org)
没那么简单
简单还容易和简约、经济(economy)联系在一起。要追求经济,就要做到参数尽可能少,结构尽可能简单,预言能力尽可能强。要构建一个理论的话,这样的要求肯定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有时候,你所研究的物理体系并不能保证你能实现这样的简单性和节约性。
历史上有一个所谓的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原则,说的就是Entities must not be multiplied beyond necessity(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什么意思?不需要的就不要往里加,越简单越好。
你为什么要经常剃胡子、刮脸、理发?没必要!胡子对你的面部重要吗?影响你吃饭吗?影响你看东西吗?所以按照奥卡姆剃刀的原则,连眉毛都可以刮掉,不影响你的主要生活质量。这就是脸部的自由参数尽可能少的例子,甚至剃个光头才好。这曾经是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些学者所遵循的指导原则——追求简单,能用两个参数来描述的东西,就绝不用三个参数。
我们讨论中微子振荡现象,最初就假设两种类型的中微子之间相互转化,用来解释太阳、大气中微子振荡实验数据。后来发现不行,需要引入三种类型的中微子才能解释所有可靠的实验数据。在一定程度上,科学不可能最开始就复杂。如果最开始就假设三种甚至四种中微子,参数就会很多。但当时只做了一种类型的实验,实验数据很少,用很多参数来描述一种现象就没意思了,就没有办法限制参数空间,就得不出正确的物理结论。所以先用最少的参数,不行的话再用次少的参数,慢慢地走向一个完整的理论。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1973年的时候,两位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小林诚(Makoto Kobayashi)和益川敏英(Toshihide Maskawa)做了一个了不起的工作。他们当时还是京都大学的博士后或助教。他们提出,基于当年的标准模型框架,要解决物质-反物质不对称问题的话,只有当时被发现的三种夸克是不够的,需要再引入三种夸克。这六种夸克构成三代,三个家族,然后才能引入CP破坏的相角,即在夸克混合矩阵中引入一个不可约的虚部。而这个虚部就保证了物质和反物之间可以有不对称——两者最初是对称的,但经过动力学演化变成了不对称。这就是著名的小林-益川CP破坏机制。
益川敏英教授后来说,他当时一边在浴缸里泡澡,一边苦苦思索这个问题。因为当时实验上确实只观测到了三种夸克,所以在简单的“三夸克”框架之内,真的没有办法让理论能够破坏CP对称性。泡完澡之后,他的想法就来了:如果再引入三种新的夸克,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有人因此戏称益川教授是日本的阿基米德。
这个小故事给我们做理论的人什么样的启发呢?你千万别老呆在办公室想着怎么做计算,没有想法的时候就去泡泡澡,或者去吃个冰淇淋,或者怎么样。李政道先生和杨振宁先生关于弱作用宇称不守恒的想法,就是在一起吃饭吃出来的——天天一起吃饭不太可能,每隔一周去一起吃顿饭就没问题了。你要做理论,一定要有理论家的风范,千万不能太死板。要经常让自己放松,这样大脑才能产生非常了不起的想法。
小林和益川教授的文章看起来很简单,但物理思想其实很深刻。这样一个工作在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词说的就是他们找到了CP对称性破缺的机制,同时预言了自然界中存在三代夸克。
 (图源:nobelprize.org)
(图源:nobelprize.org)
大家想一想,当时只有三种夸克,为了解释理论中可以包容CP破坏效应,需要再引入三种新夸克,然后引入四个自由参数——在当时完全没有任何实验证据的新参数。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你敢这么做吗?换成我的话,我肯定不敢。对我来说,引入一种新粒子,引入一两个新参数就已经觉得很不经济了,就会担心别人会不会相信我的理论模型,以及我的文章能不能被接受发表。
而他们一下子引入了三种新夸克,四个未知的参数,其中包括三个混合角和一个CP破坏相位。这在当时来说,毫无疑问是非常大胆的预言。但是很幸运,他们走在了正确的路上。最终实验证明他们的预言都是对的。
这就启示我们,做理论家要有品味,要有格局,在追求简单的同时,更要追求整个理论的完整性和它的预言能力。有时候做假设,引入一些新粒子、新参数是必要的,但很多时候可能是不必要的。这时候,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权衡,要看自己付出的代价值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