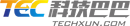广州湾:名字里的误会 建筑里的沧桑 一个被“租借”出来的城市传奇
2026-02-20 07:02:31 人民网 观点
文/金思宇(文化学者,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
丙午马年正月初三,南国海风温润如绸。我没有选择乘坐游轮出海观光的常规路线,而是执意走进了霞山的广州湾法国公使署旧址,而后穿行于赤坎老街的骑楼巷陌之间。那一刻,我明白自己并非在度假,而是在进行一次迟到的朝圣——朝圣一段被岁月掩埋、却从未真正远去的城市记忆。当指尖触碰公使署斑驳的墙体,当目光掠过老街骑楼的拱券廊柱,一个问题油然而生:一座城市的记忆,究竟以何种方式镌刻于建筑之中,又如何在时间的冲刷下,凝结为可供后人解读的文化密码?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地方,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历史的“误会”——它叫“广州湾”,却不在广州,而在湛江。这像极了“北京烤鸭”并不诞生于北京的幽默逻辑。然而,这个名字的错位,远非地理概念上的张冠李戴,它恰恰是广州湾百年沧桑的起点,浓缩了中国近代史中一个边缘港口如何在列强博弈的夹缝中被迫“长大”的独特命运。
一、名字的误会:从地理俗称到殖民烙印
在19世纪末以前,“广州湾”不过是广东沿海渔民对雷州半岛东北部一个海湾的朴素称呼。文史资料记载,明清方志舆图中的广州湾,最初所指当为吴川县南三都田头岛、北颜岛南端与地聚岛所形成的一处海澳。因位于广州出海航线之上,风平浪静,便成了天然的避风港,渔民们习惯性地称之为“广州湾”。彼时,这片土地分属高州府的吴川县和雷州府的遂溪县,行政上与广州府并无关联。
历史的转折发生在风雨飘摇的1899年。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法国人看中了这个深水良港,以“停船趸煤”为名,胁迫清政府签订了《广州湾租界条约》,租期99年。条约虽在字面上虚伪地声称“于中国自主之权无碍”,实则将约2130平方公里土地与海域的治权完整让渡给法国,广州湾被划入法属印度支那联邦范围。法国人将其命名为“白雅特城”(Fort Bayard),试图在此复制一个“东方的马赛”。
这个地名的“误会”,实则是历史的无奈:在弱国无外交的时代,一个地方的命运往往不由本地人决定,而是被远方的政治力量随意命名和摆布。正如学者所言,这种“主权虚置”与“治权独享”的制度设计,堪称殖民法理操纵的范本。闻一多先生在《七子之歌·广州湾》中,将广州湾比作神州的“后门铁锁”,东海和硇洲两岛喻为锁上的一双“管钥”——这诗意的譬喻背后,是主权旁落的锥心之痛。
二、双城记:赤坎的烟火与霞山的洋气
广州湾的历史,在地图上呈现出一种有趣的张力:一边是赤坎,一边是霞山。这两个世界,构成了广州湾文化最核心的二元结构。
赤坎,是“活着”的广州湾。 它当时未被划入租界核心区,保留了最浓郁的广府与闽南烟火气。宋代已成雏形的赤坎,清康熙年间解除海禁后,闽浙、广潮、琼崖等地商户纷纷至此经商,逐渐发展为繁荣商埠。走在赤坎的骑楼下,岭南传统的木雕灰塑与受西方影响的拱券廊柱交错共生。这里的故事,是本土商人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奋斗史。以许爱周家族为代表的商界力量,利用租界带来的贸易便利,将赤坎打造为粤西最繁华的商埠,一度博得“小香港”之名。1925年落成的广州湾商会会馆,仿法国钟楼样式设计,至今仍屹立在民主路,无声见证着那段民间商业的韧性与辉煌。
2024年10月,广州湾国际通道馆在赤坎老街6号码头揭幕,总面积约200平方米,以数字化、档案化、图像化的方式,原始资料来源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等权威机构。这座新落成的文化地标,正是对赤坎商贸历史与抗战贡献的当代回响。
霞山,则是“权力”的广州湾。 这里是法国人的大本营,是行政、军事与文化的中心。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者蔡为哲的研究揭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现今被命名为“广州湾法国公使署旧址”的建筑,实为1913年建成的白雅特城旅馆,而“法军指挥部旧址”则是1921年的总公使邸。这两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在百年之后被后人重新命名、赋予新的历史意义——这本身就是历史叙事的生动隐喻。
1903年建成的广州湾法国公使署,钢筋水泥结构三层,建筑面积1902平方米,呈近代西式建筑风格。楼顶自鸣钟报时,正门弧形台阶直通二楼,极具法国新古典主义风格,宣告着殖民者的权威。与其相邻的维多尔天主教堂,双尖石塔巍峨高耸,是当时华南地区最具规模的哥特式教堂。然而,这份“洋气”背后是冰冷的现实——那些如今被游客视为“网红打卡点”的洋楼,在当时是特权的象征,是普通中国人不得随意进入的“禁区”。
三、学术的烛照:近年的广州湾研究新视野
近十余年,广州湾历史研究迎来了学术上的“黄金时期”。2012年至2023年间,学界运用新史料与新方法,在诸多方面取得可喜成果。其一,基于历史档案,深化了中法外交博弈与地方抗法运动的内在机制研究;其二,中国共产党在广州湾的宣传组织与抗战时期广州湾的战略地位研究取得新进展;其三,以货币史、医疗史等为路径的研究,深化了广州湾租借地治理体系、社会生活与历史人物的复杂图景。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口述史方法的引入。2023年,学者吴子祺主编的《口述广州湾:近代租借地历史的多元叙事》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部420页的著作分为七大部分,采访了昔日法国管治时期的亲历者、亦官亦商的“法国师爷”、汇聚四方的商人、多元市井的居民,以及逃难广州湾的战争幸存者。吴子祺曾在香港中文大学研读历史学,后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深造,从法国多个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了大量殖民与历史档案。这种“向下看历史”的方法论自觉,使得广州湾的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条约文本,而成为有温度的个人记忆。
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国家主权的本质不在条约文书,而在人民捍卫每一寸土地的意志之中”。口述史的价值,正在于它让那些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个体声音得以浮现,让历史的多元面向得以呈现。
四、抗战“孤岛”:血色通道与民族大义
广州湾历史中最悲壮也最传奇的篇章,莫过于抗日战争时期。
1938年广州沦陷、1941年香港沦陷后,广州湾因其法国租借地的特殊国际地位,成为当时中国南方唯一未被日军封锁的出海口。在中国战场上,陆有滇缅公路,空有驼峰航线,海有广州湾通道——这条国际通道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独特贡献。2024年揭幕的广州湾国际通道馆,正是以抗日战争时期经济作战的独特视角,凸显了广州湾国际通道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时间,广州湾呈现出畸形的“不夜港”繁荣。大量抗战物资——药品、汽油、武器——经此转运内地;大批难民与文化名人,如茅盾、夏衍、陈寅恪等,也经由这条通道转移,在赤坎兴办教育、开展文化抗战,为保存岭南文脉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这种繁荣是短暂的。1943年2月,日军武装登陆广州湾,法军未作抵抗,日法签订《共同防御广州湾协议》,完成了主权交易的肮脏一幕。1943年至1945年,广州湾法国公使署沦为日本占领军军部。日军随即设立宪兵队、慰安所,强占民田,实行法西斯统治。在此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成为湛江抗战的精神灯塔。1938年成立中共广州湾支部,遂溪县青年抗敌同志会迅速发展至5万余人,掀起抗日救亡高潮。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相继组建,在沦陷区展开敌后游击战,用血肉之躯在主权裂隙中捍卫着民族的尊严。
五、多元文化的“混血”遗产
广州湾近半个世纪的殖民历史,为湛江留下了一份独特的“混血”文化遗产:
建筑文化:湛江保留了中国规模较大的法式建筑群之一。从1903年的公使署、1900年的警察署,到1899年建成的硇洲灯塔——后者与伦敦灯塔、好望角灯塔并称世界三大灯塔,以无泥浆麻石堆砌工艺见证着百年匠心。高19.2米的硇洲灯塔建成于1902年,塔身用岛上麻石砌成,塔内由68阶围绕中心石柱依次错开、螺旋而上的台阶围绕而成,仰俯之间,犹如折扇半开。灯塔透镜由139条弧形三棱镜片组成的两个抛物面,工艺巧夺天工,是全球现存的两座牛眼水晶磨镜灯塔之一。
位于霞山东堤老街窄巷中的西营鱼市场旧址,则被建筑学者视为被严重低估的近代建筑,是国内仅存的近代钢筋混凝土大型圈梁结构的专业水产市场。1937年建成时因其顶部椭弧形拱顶呈八角形亭盖状,又被称为八角楼,内部面积963平方米,由10支砖砌方柱托圈梁构成三层八角面椭弧形结构,体现了当时国内大跨度建筑的顶级建造水平。
2013年5月,广州湾法国公使署旧址联合广州湾法军指挥部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建筑融合了岭南的通风防潮与欧洲的装饰艺术,是“中西合璧”的活化石。2025年,湛江市博物馆持续开展“漫步广州湾”专题展览进校园、进社区活动,引导公众思考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模式。
饮食文化:法式面包与咖啡的喜爱,深植于湛江人的味觉记忆。文化保育者吴子祺在《口述广州湾》中记录的老人杜仲浩,晚年最爱喝加了很多糖的咖啡,那是属于广州湾时代的味觉乡愁。如今表皮酥脆的牛角包,已成为湛江早茶的特色符号。威化饼之名,源自粤语对“华夫”(Waffle)的音译,湛江华威饼干厂曾是全国首家威化饼研制企业。
老街活化:今天的赤坎老街,依然活着。2020年起,赤坎区实施古商埠保育活化工程,采用“微改造”方式,投入约1.3亿元国家专项资金,将染坊街、广州湾商会会馆等改造为文创空间。2026年初,“船屋”焕新亮相——这栋形似远洋客轮的百年建筑,原为广州湾时期的六国大酒店,见证了商埠的万商云集,融合了中西南洋的建筑风格。此次改造将其纳入古商埠保护工程,既守住了“不可移动文物”的底线,又通过功能活化让历史记忆鲜活,走出了一条“以用促保”的可持续之路。
2024年7月,赤坎老街商会正式成立,探索“居民产权+商会统筹+专业运营”的新模式。老街的魅力,正在于它既是历史的标本,也是生活的现场——水井头的海鲜捞粉香气氤氲,骑楼下阿婆的蒲扇摇着湛江白话的三餐四季。
六、历史的回响:从“广州湾”到现代化港口城市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中国政府根据《中法交收广州湾专约》收回广州湾,同年9月21日建湛江市,市政府驻原法国公使署旧址。1949年湛江解放后,市人民政府亦曾驻此至1954年。这个新名字,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发展,从殖民伤痕到主权重塑。
今天的湛江,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2024年,湛江港完成货物吞吐量1.07亿吨,集装箱吞吐量132万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作为连接“一带一路”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支点,湛江正以40万吨级深水码头、宝满集装箱扩建工程,续写着百年港城的崭新篇章。
然而,现代化并未割裂历史。硇洲灯塔的牛眼透镜仍在夜海中投射光柱,八角楼的拱顶依然承载着市井烟火,公使署的石阶上走过一代又一代寻访历史的游人。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没有记忆的城市是肤浅的,应该说,湛江的城市雏形是从沦为法国租借地后才开始的。遗留下来的历史建筑,为我们勾勒出湛江成长的轨迹”。
我在正月初三的午后离开老街时,看见几名穿汉服的少女在骑楼下拍“簪花”照,本地阿婆在隔壁摊叫卖着虾饼。那一刻,叫卖声、快门声与百年前商号的喧嚣重叠在一起,让我忽然明白——所谓历史,从不是封存在玻璃柜里的旧物,而是仍在呼吸的日子。广州湾法国公使署的钟声早已沉寂,但历史的回响,仍在每一块麻石、每一道拱券、每一个湛江人的味蕾与记忆中,生生不息。
广州湾的历史文化叙事,是一个关于“边缘与中心”“屈辱与荣光”“冲突与融合”的故事。从地名误读到主权回归,从殖民伤痕到文化混血,这段历史让湛江不仅拥有了迷人的海滨风光,更拥有了深沉的人文底蕴。一座城市的传奇,终究写在它的建筑里,融在它的味道里,更刻在它的记忆里——而这份记忆,正等待着每一个走进它的人,去倾听,去理解,去传承。